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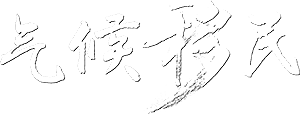

气候移民
当偏房的屋顶被七手八脚掀落的时候,马国清一家新的生活就要仓促开始了。他只是拿到一个有地址有门牌的新房钥匙,而对新家是什么样一无所知。那天是2013年12月清冷的一天,政府雇来的搬迁车队停在村口,此时距离人们得到确切搬家通知不过两天,大多数人都只能像他那样象征性的收拾几样家具:床、柜子,几件衣物和一袋土豆。就这样,浩浩荡荡的搬家队伍从宁夏南部山区向北部平原出发,留下处处是残缺旧屋的村庄。
马国清今年31岁,他和父母妻儿生活在宁夏西吉一个叫芦子窝的村里。他还有3个儿子,分别只有7岁、5岁和不到周岁。跟村子其他年轻人比起来,马国清说话做事甚少犹豫。搬家的前两月,当乡政府通知他去签搬迁协议时,他甚至都没看文本便落了名。
“外面地方平,用水方便,小孩读书方便,我考虑什么?”他说。
马家的搬迁,源于宁夏一项涉及35万人的移民计划。这份叫做宁夏“十二五”中南部生态移民的规划中写到:迁出地“处于我国半干旱黄土高原向干旱风沙区过渡的农牧交错地带,生态脆弱,干旱少雨,土地瘠薄,资源贫乏,自然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
从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银川平原向南,便进入规划所指的黄土高原区。从卫星地图上看,宁夏地势南高北低。北部的贺兰山由南向北,扼守沿山洪积平原,由青藏高原发源的黄河过黑山峡,河面豁然开朗,自此大致沿着贺兰山的走向,纵贯整个宁夏平原,造就了“天下黄河富宁夏”。然而在这个南北狭长的自治区南下,穿过引黄灌区,则是由风沙统治的王国。在春天来临之前,那里是一片单调干涸的黄土坡,不长其余颜色,车子急驶而过,风在窗外夹着泥沙旅行,然后落在深陷的沟壑里,不着痕迹的改变着地貌。
就是这块干涸的黄土高原,亦是我国连片扶贫区之一,生活着回、汉等民族。它有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西海固。
“中国西北干旱环境早在晚白垩纪和早第三纪就开始形成,并不是短期内造成的。”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汪一鸣说,“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之后青藏高原大幅度隆升,干旱程度就加剧了。”
不过,如今的全球气候变化似乎使事情向更糟的方向发展。
根据宁夏气象局的研究,近50年那里的平均气温上升了2.2℃,干旱及其它极端气候事件也比过去来得更加频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认为,全球海陆表面平均温度在过去130年间升高了0.85℃,而宁夏的变化显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气温上升有可能会使未来降水增加,但宁夏所处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区生态脆弱,这使得气候专家林而达认为升温同时会导致蒸发增加,可能抵消甚至超过降水量增加的作用,无助于解决干旱缺水的程度,也就使得世代生活在那里的人面临着维持生计的困扰。
一项由中英瑞三国于2010年联合开展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研究显示,宁夏中南部为雨养农业,农田除了靠天吃饭,缺乏灌溉水,而随着气候变化,一来粮食亩产呈现递减趋势,仅为30公斤左右,不足黄灌区的1/10,二来气象灾害造成的粮食产量损失呈不断上升趋势。
在马国清父亲马炳武的记忆里,西海固从1970年代开始雨水就愈加少,1990年代中,水少到一根草也不长,庄稼全部绝收,为了不让家里人饿死,他只好带着年幼的马国清一路行至银川乞讨。
家里的晚餐是简单的土豆面——西海固最常见的主食,暗黄的灯光照在屋里,一家人围坐在短腿桌旁,孩子的眼睛则盯着电视眨也不眨,这是除了电灯外家里唯一的电器。妻子马晓红从县城捎回来几样蔬菜,放进沸水和辣椒一煮,给晚餐增加了滋味。绿色蔬菜在村庄的饭桌上并不常见,就连串门的叔叔都说这是芦子窝最丰富的晚餐。马国清还记得随父亲行乞的景象。“我那时候就想,以后要每天都能吃上一碗土豆面就好!”
把像芦子窝这样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贫困人口迁出,便是宁夏所采取的应对战略之一。如果按照国际移民组织的定义,这部分人则是事实上的气候移民。
该组织发布的《2010国际移民报告》中指出气候变化可以从以下方面影响人类的迁徙:持续增温及干旱影响农业生产,降低生计水平和清洁用水的利用,导致人们被迫离开家园;又或者因为气候变化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人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导致社会冲突和人口流动。
在芦子窝,尽管没有人知道这个词,但国际移民组织在2013年预测,在今后的40年里全球将有2亿到10亿人成为气候移民,如果以今天的人口规模来算,这意味着全世界每100个人中就有2-14人加入这一阵营。
在中国,如果把西海固这样的生态脆弱区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中提到的连片特困地区、重点县和扶贫村放在同一张地图上,会发现它们在地理上有惊人的重合。环境保护部2005年统计显示,中国95%的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地区,而这部分地区对气候变化更为敏感。
关注于抗击贫困的非政府组织乐施会在中国注意到了全球变暖与贫困问题的关系,他们的报告直陈:气候变化将直接或间接加剧贫困,而国家应当加大相关气候变化适应对策及技术研发的投入,并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将适应气候变化与扶贫结合作为中的议题加以讨论,以达成一个真正关注贫困人群利益的协议。
最后通牒
芦子窝的名字来自于山沟里一窝野生的芦草,它们在落了雪花一样的盐碱地里生长。山坡上散落着四四方方的民居院落,他们逐渐取代传统的土窑,而后者大多已成为牛羊的圈所。山谷里偶尔传来年轻人们追捕野兔的奔跑声和笑声。除此而外,乡村生活实在乏善可陈。
芦子窝位于宁夏南部固原市西吉县,人口50余万,据省会银川370余公里。那里是陇西黄土高原的腹地,东部六盘山所发挥的小气候调节作用有限。在西吉,干旱经年累月,初来乍到的人,直觉得嗓子眼儿都皱起来,就像裂开的黄土地。
那里有多旱?西吉气象局的统计表明,西吉年均降水量为200-650毫米,蒸发量1500-2000毫米之间,蒸发量大大高于降水量。
水是村庄的头等大事。西海固的俗语说:喝一口水,眼泪汪汪,饮一瓢水,就是天堂。赶驴挑水,是每家每户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
细小的山泉在峡谷的深处,沿着曲折陡峭的山路要走40分钟。近的地方还有一眼泉,流出来却是苦咸水,只有牲口能喝,远的泉才是清水,人可饮用。话这么说,可马国清用“清泉水”泡茶,在外人吃起来,杯盖里仍旧是苦味。



根据西吉县水务局的调查,这里的地下水溶解性总固体和硫酸盐超过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数倍。在县城里的人家都购买外来的纯净水使用,在村里,人们只好守着传统生活。
马国清匐在蓄水池口,全身弯下去一桶一桶把水舀上来。蓄水池口又低又滑,他的母亲有一次就失足整个人掉下去。接好水以后,准备赶着驴回去,但他的驴好像怕人再让它负重,还没等水桶盖拧紧就要跑,马国清大喝了它一声,结果驴跑得更快,人只好小跑,跟着驴赶路。
除了挑水,户户都要造水窖,水窖的外形四四方方,通过收集地面、屋顶的雨水并存储起来供人畜使用。
马国清家里的水窖能装8、9吨水,足全家5月之需。”这要是在你们城里,还不洗几次澡就没了?“他说。

妻子马晓红出生在西吉县城,2006年他们结婚时,她的弟弟来送亲,到了亲家屋门前,一看这惨淡模样,不禁替姐姐抹眼泪。这也是马晓红第一次来芦子窝,马国清早跟她说:“我只有两间屋、一头牛给你。”结果她答说,“再怎么样,看上的是你的人,又不是你的家。”
也不是每个人都像马国清这么幸运,曾经就有西海固人娶了外来的媳妇,娘家人嫌弃村里穷,硬是把新娘给带走了。
虽然外面的人不愿来,但西海固的人口之多及由此导致的资源匮乏又是大问题。
据研究宁夏人口变迁问题的杨新才讲述,在上世纪40年代末,由于清朝末年回民起义遍及西北,及至几十年战后恢复,西海固人口不足20万人。随后又经过民国烽火和地震等灾害,到上世纪40年代末,人口增加,但总数也不足50万人。相比较,现在仅西吉一县就有50余万人口。
曾任宁夏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马忠玉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国家土地管理局,还有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估算,宁夏中南部地区的人口承载能力只有130万人左右,但是现在当地人口已经230万人了。超载会导致更加贫困,环境更加退化。所以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宁夏一定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汪一鸣明确支持移民主张。他说,宁夏的中南部是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人,通过移民来缓解当前的环境压力,也能尽快让老百姓摆脱那些不具备生存条件的土地,走出贫困。
2011年“十二五”生态移民计划启动,芦子窝被列入搬迁名单,接收他们的是500公里外、宁夏北面的村庄庙庙湖。
实际上,许多西海固人从1980年代开始就自发向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银川平原一带迁徙。在1983年,宁夏政府开始号召南部山区的贫困人口向北部迁徙,并在黄河灌溉区进行拓荒,开始新的生活。
从2001年开始,宁夏政府提出“生态移民”的概念,和前一阶段的移民不同,这一阶段强调生态修复的功能,强调移民不仅仅是为了扶贫,也为了重建迁出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宁夏扶贫办的统计显示,自1983年以来两个阶段共移民78.58万人。
按照规划,迁出地要实施生态修复,要求自然村或行政村整体搬迁,为了让村民能尽快搬走,才出现了一开始政府要求拆房一幕。不能马上搬走的,也要拆掉一部分。宁夏移民局副局长郭建繁说,过去没有这个政策,出现了移民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两头生活的情况,给人口管理和生态修复都带来了很多问题,为了让人不再两头摆动不得已就要拆房子。
回到芦子窝,就是否应该搬迁,留守的中老年人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形成了不同的阵营。
北方民族大学教授范建荣一直关注宁夏移民问题。他对“十二五”移民的研究发现,中老年搬迁意愿并不强烈,有的是因为对外界的适应能力不如年轻人,而有的则是因为“故乡情结”。
马国清的叔叔、45岁的马存子是主张留下的人之一。他的院子在山头,往下一望是深深的峡谷。四季更迭、天地苍凉,于他,都是院外的风景。
尽管政府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但马存子仍没有放弃留守的念头。春播一到,他拎着土豆和小麦种子又上地里去了。
马存子的儿子马存宝20岁,要不是去年在外与人起冲突腿上受了伤,他不会提前返乡。村里的年轻人们都陆陆续续搬了家,他终日无事可做,只好盯着手机网上与人聊天。马存子也知道儿子的心意,这个四处是断壁的乡村托不起儿子的城市梦,去了庙庙湖就离银川更进了一步,但他要考虑全家人的出路。
马存子也不是没有那样的梦想。1995年西吉大旱,他领着全家投奔远嫁新疆的姐姐,不想那一年移民计划遭到挫折,开垦的棉花地没有收成,等到1997年西吉下了雨,旱情缓解,马存子思前想后,决定又返回西海固。
“在外面过得不容易,经过了那次,才想着安稳一点,不要往外搬。”他说。
生态修复
西部的民歌调子《花儿》有一曲如此唱到:沟岔里的水干了,我的嗓子干得冒火了。在西海固,干渴的又哪里仅仅是人。
芦子窝的山泉在几十年以前还不是涓涓细流,80岁的老阿訇马德录清清楚楚的记得。他们一家是村里最早的定居者,他听他的长辈说,一家人于1894年从甘肃逃荒而来。祖爷爷来的时候,就是看这里有泉,便在黄土坡上修了土窖住下来。再后来,才慢慢有了其他家庭,从一户到一组再到一村。
给芦子窝带来最大改变的还是垦荒。马德录说,人民公社时候,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把能开荒的山头都开了。
“泉水原来不小,过几年就不行了,高处的没有了,又在低处挖。”他用细小的声音说。
离开农村到西吉县城,发源于宁夏月亮山南麓的葫芦河只剩下干涸的河床,孩子们只知道它的名字却没见过它的样子。
西吉自来水公司的经理高玉杰因为与水打交道而对此深刻,”在20年以前,葫芦河岸还有很多树,我小时候还在河里玩水。“高玉杰将此归罪于过度的开发和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受困于水的地方,在去年底县城才刚刚有了远调而来的自来水,过去,县城靠着地下水运转,这些地下水不仅在各项指标上都达不到国家生活用水标准,而且停水2、3天甚至更长都是家常便饭。
干涸的河道在一些地方成了种植西芹的农田,过去几年西芹价格看涨,这种需要大量水供养而生长的蔬菜在西吉得到了大力推广,县政府甚至将其作为与土豆这种抗旱作物同等重要的优势产业。高玉杰无奈的说,”我们研究水的人都知道发展西芹是个问题,但它又确实在农民增收上作用很大。“
2003年夏天西吉遭遇暴雨,葫芦河河床20年来首次有了流水,暴雨把浑黄的泥浆冲得七零八落,当地媒体以”干涸的河床长出了水草,两岸绿意盎然“来形容那时景象,不过这只是昙花一现,一时的暴雨不仅没能拯救葫芦河,还造成了西芹和其他农作物减产。
脆弱的环境迫使人们利用更多的自然资源扩大生产,而这种生产又反过来导致环境愈加恶化,形成了所谓的PPE怪圈——贫困、人口、环境互为因果关系。
对此,汪一鸣说,移民,就是让自然资源的承载量逐渐回归到一个合理的水平。迁移不代表退缩,人与自然之间,需要这样的妥协。
钻研西北生态问题的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宋乃平在迁出区看到了改变。根据他的研究,年降水量300毫米是宁夏干旱、半干旱区生态修复的临界点。300毫米以上,自然界的修复能力较强,不需要人工干预,植被生态在一定时间就能得到恢复;而300毫米以下的地区,则需要人工干预。
“降水和土壤状况好一点的地方自然能恢复到什么样?基本上植被覆盖一年就能恢复60%。”宋乃平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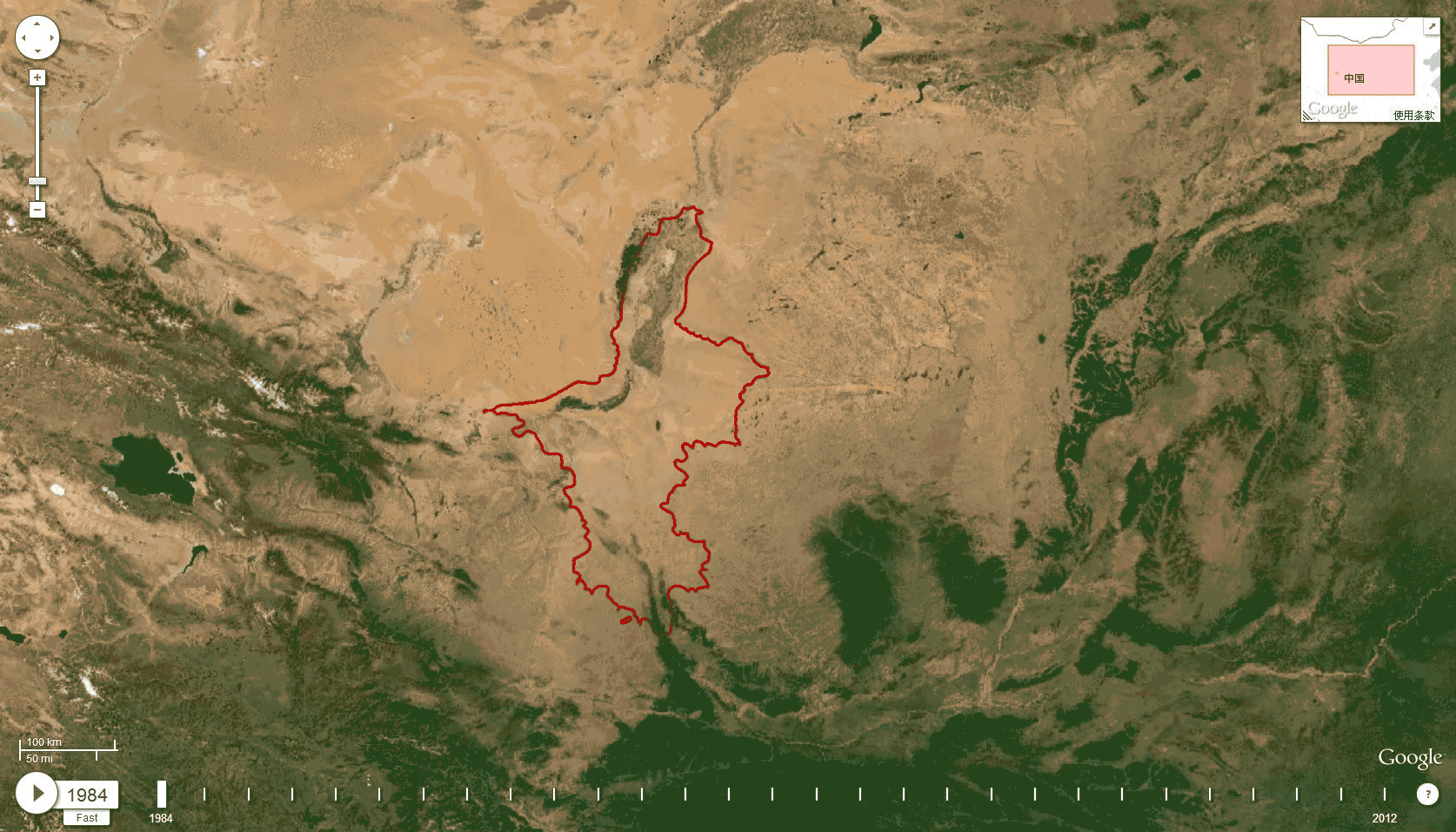


宋乃平通过遥感技术观测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解析宁夏植被覆盖率和气候与人为活动的关系,并期望为宁夏的生态修复提供经验。植被的生长虽然与自然因素休戚相关,但一些地方的研究表明,尽管有的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并未增加,甚至略有降低,但封育草场的人为努力还是增加了植被覆盖度。在有的地方,因为植被的恢复,小气候也得到改善。
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位于宁夏东部的盐池县。盐池位于宁夏中部干旱带,许多村子就在毛乌素沙地边缘。那里自2000年开始实行禁牧、苜蓿种植等生态修复措施。遥感技术能够帮助人们分析区域植被变化,而监测数据显示十几年来盐池县的植被覆盖度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依据过去的生态修复经验,在迁出地,移民政策着力于通过减少人口对资源的使用和破坏来维护生态。宁夏的计划是,退出了人和地,就要对土地实行封禁管护,而在少数有条件的地方,则实施人工种林种草工程,重建稳定的林草生态系统,提高森林碳汇和水源涵养能力。
宁夏《生态移民迁出区生态修复工程规划》中说,“十二五”移民将退出土地700万亩,占迁出区土地总面积的12.4%。这份规划认为:迁出区处于西北重要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防风固沙生态功能区,是西北东部重要的生态屏障,因此修复和保护这里的生态尤为重要。
人退草进,此消彼长。
在西吉其他的村里,那些已经搬出了一年以上的地方,苜蓿和不知名的野草已经在暖暖的空气里露芽。
新村困境
留守在芦子窝的人还在等着政府“最后通牒”,村子越发冷清,过一天是一天。而在宁夏的另一头,新村庙庙湖已经是人声鼎沸。
在距离黄河岸仅仅数公里的毛乌素沙地边缘,成百上千的房屋和院子从一片荒芜的黄沙中被建造起来,它们的外观差别之小,以至于那些最早的居民,即便搬来大半年的光景,也常常要靠数门牌号来辨认方向。
庙庙湖位于宁夏北部石嘴山市平罗县,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相邻,由银川驱车向北100公里,再跨过黄河便是。按照规划,它一共接纳西吉移民1414户、共计6800人。


2014年初,清真寺还只是在彩钢房里的临时设施,针对女人和小孩的学习班已经办起来了,念诵《古兰经》的声音一阵阵传来。阿訇马应成说,搬来后一些农民无事可做,有的人连宗教基本常识都不懂,这一组织起来,对村秩序也有好处。
马国清的新家在庙庙湖七区,因为房屋对于三代同堂的家庭来说太小,他决定在扩建屋子前让父母先搬进来。
他的母亲马翠芳搬来了几个月,却因为不识字也不认得几个邻居,轻易不敢离开村子。阳光好的时候,她背着手在四分大的院子里来回踱步。
“心里闷得慌呗,就在院子里走。”她说。
“为什么闷得慌?”
“老家有牛可以养,这里什么事都没有。”她答。

可是这些话马翠芳都忍着不告诉儿子。荒漠上的风一吹,丈夫马炳武的手背上开裂了,过去多少年在山村里都没有过,也没告诉孩子。
嘴上一个劲儿说好,儿子打电话来的时候,马炳武却忍不住在电话一头偷偷抹眼泪,他总惦念着家里的牛和农田,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这里变成了“没用的人”。
按照移民安置政策,政府分给村民的耕地应为人均一亩。但是这些耕地在移民还未入住前由乡政府承包给外来的企业。平罗县移民局解释说,这是考虑到统一经营有更大的收益,这些收益也会还之于民。
马炳武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到菜市场转了一圈,什么也没买,回来闷声的说,“这里的菜比我们西吉贵着呢!土豆家里5毛,这里一块(每公斤)!”
年纪大的人高兴不起来,年纪轻的人也在担忧自己的未来。临近入春招工的季节,这种焦虑像传染病一样在年轻人中蔓延开来。村支书的家里挤满了人,都是来打听招工信息和反映各种困难的。“政府把我们搬过来了,可现在我们就觉得像一盘散棋,不知道该怎么走了!”不知道谁在人群中冒出这样一句话,引起人附和。
庙庙湖村委会的招贴栏提供附近工业园区的招工信息,却鲜有人看。这一天早上,平罗县劳动就业服务局派车组织村里人到周边的工业园区参观,28岁的马兵匆匆的吃好早饭准备加入他们。
马兵从小没有念书,招贴栏对他来说就是天书。2004年他参加西吉县的劳务输出,被介绍到北京郊区家禽屠宰场上班,在那里他和未来的妻子李虎叶相识。2010年他们的孩子到了要上学的年纪,夫妻两就回了老家。
马兵和李虎叶都羡慕那些能在北京生活的人。他们在屠宰场的时候,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连周末和节假日也不能休息。工资高的时候,一个人每月赚2500块钱。虽然在北京住了这么多年,但他们到市区的时候寥寥可数,“就看过一次天安门,出门还要花钱,得省着点。”李虎叶说。
因为没有自来水,他们结婚时买的洗衣机在芦子窝从没用过,在新村总算派上用场。马虎叶兴致勃勃的往洗衣机里倒水,依照提示设定洗涤时间,机器转了几次,衣服却洗不干净。


串门的人提醒她水放得太少,马虎叶这算是第一次知道洗衣机的正确用法,她自己都乐了。“我不知道要这些水!”她说。
马兵跟着政府组织的参观队伍到了工业园区,负责就业安置的工作人员开始说园区如何如何好,跟他们的老家西吉比起来工业是如何发展,马兵只是看着那些高大的烟囱沉默不语。他听说在园区找工作也不容易,他的很多同龄人甚至根本没想过有一天能进入工厂。虽然他看不懂,但是村委会提供的就业信息上绝大部分岗位都注明要高中或同等以上学历,能够读书认字是最起码的要求。
一份由平罗县劳动就业服务局提供的庙庙湖移民调查表揭示了这里存在的问题。根据这份调查表,整个村已经移民的6026人中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86人,占总人口1.4%,其中有很多是在读的学生,文盲1088人,占总人口18%。根据平罗县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平罗拥有精细化工、多元合金等产业园,享有国家“十佳最具竞争力市县”、“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县市”的头衔,这里2013年的地区生产总值125亿元,是西吉41.5亿元的3倍还多,平罗的经济依赖于工业发展而非农业。
劳动力市场的人才结构矛盾并不是平罗所遇到的个案。根据银川市政府2013年6月对移民家庭的统计,在“十二五”期间已经搬迁的26017人中,文盲、半文盲占搬迁总人数的15%,初高中以下文化占78%;大中专仅占搬迁总人数的7%。在整个宁夏自治区,2013年,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率为7.74%,人均受教育年限8.56年,这高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文盲率4.08%(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占总人口比率)。
“一方面是招工企业找不到合适的人,另一方面很多移民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县政府也组织了很多培训,关键还是要移民转变观念,提高自身的素质。”平罗县劳动就业服务局的王兴龙说。
因为文化程度偏低,有的移民不得不从事任务繁重或是高污染的工作。在庙庙湖附近的移民村三棵柳,48岁的移民明耀虎就不得不在镁厂从事高强度的工作。“一天下来浑身都痛,不吃安乃近(解热镇痛药)睡不了觉。”他说。
在这个村子,一些移民安置房空闲下来,因为在新环境里找不到工作,有的人回到老家投靠亲戚;少数的空房又很快被从更偏远地方来的移民承租下来,带着对新生活的计划和向往。
但是,迄今没有一份官方的统计显示有多少移民返贫或返回原住地。在学术界,政府采取切断移民与原居住地联系的”断根“方式却引发了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展与环境研究所博士后孟慧新在考察了气候移民案例后说,人口流动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宁夏的移民规划对移民迁入和迁出行动的管制,不认可移民通过流动进行的自发性调适,使得移民定居和就业的不稳定与社会保障的缺失互相强化。“如果移民不能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适应气候变化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她补充道。
宁夏“十二五”移民规划里提出让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口号。但是由于就业市场的供需矛盾存在,宁夏移民局副局长郭建繁承认,要真正让移民稳得住,仍然是考验决策者的难题。












